The Fundamental of Ethics, Chapter 10, Shafer-Landau
效益主义的弊病
福祉的计算
效益主义要求我们在作出抉择时,计算出行为产生的 1) 福祉 2) 痛苦,得到 3) 善恶比,并比较这个行动是否能取得比其他行动更优的善恶比。
但有人反驳,「计算福祉」(同样的,痛苦)从原则上就是不可能的。
首先,我们并不能总是掌握一个行为的所有可能效益;有些行为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越了一个人的生命尺度。效益主义者回应,这仅仅说明了我们的道德无知(moral ignorance),如果掌握了足够的信息,至少福祉的计算是可能的。
其次,这一方法论和多元主义的幸福观(pluristic view of well-being)相冲突。后者认为,个人福祉有很多来源,常见的候选包括知识、美德、爱、友谊、幸福、自主等等。
我们该如何计算「爱的程度」,「友谊的程度」?如何又将这些品质加权合成一个总体的个人福祉程度?即使它们能够计算,但不同特质之间真的能够通约(commensurable)吗?
这些问题能总结为如下的《论价值计算》(Argument from Value Measurement) :
- 效益主义为真仅当存在一个精确的计算标准,能够决定某个行动的后果的效益。
- 该计算标准不存在。
- 因此,效益主义为假。
效益主义者难以驳斥前提 2(直到现在他们都无法证明这样标准的存在),可以下手的就只有前提 1 了:即,即使我们没有这样的计算标准,效益主义也可以为真。
考虑这两种痛苦:1) 丈夫在孩子面前辱骂妻子 2) 贫民窟爆发了大规模瘟疫。我们虽然无法用精确的标准对这两种恶进行量化,但却能做出第二种痛苦「更大」的判断。也就是说,至少在某些情况下,福祉和痛苦是可比较的;而一旦可以比较,效益主义就仍行之有效。
一招险棋!效益主义没有被推翻:然而以上这些所有问题都能令我们意识到,我们一方面是道德无知的,另一方面,即使能够了解所有行为的结果,我们也难以进行精确的计算与衡量。若如此,效益主义就失去了它最主要的一项优势,即提供具体指导的实用性方面。
苛求的行动指南
深思熟虑 deliberation
按照效益主义的要求,在做决定之前,人必须掌握充分的道德知识和卓越的「计算」技巧。
反驳:密尔的经验论:「基督徒无需在每次做决定前都读一遍圣经」。动机 motivation
效益主义以「最大化世界总体福祉」为唯一目标。但人非圣贤,我并不想在做出每个决定之前都得考虑我的行动是否「最优」。
妥协:的确如此。并且效益主义者承认,真正怀抱这一目标的个体反而常常失败。一个思考的角度是将决策过程(decision procedure)与正确性标准(standard of rightness)区别开。效果论首先是一种正确性标准。它关注的是合理性,旨在解释某个行动为何、在何时被认为是「正确」的。而效益主义所遵循的效益原则(principle of utility)是基于效果论的决策过程,用于指导具体行动。重点在于,
行动 action
即使我们真正了解到能够「最大化世界总体福祉」的那个行动,我们又为何要去做呢?而效益主义认为,这是一个人「应当」去做的。
显然,我能确信现在将我的零花钱全部捐给 UNICEF 能够增加世界总体福祉,如果选择回应效益主义的要求,我这辈子都别想去旅游了。
对于超义务(supererogation)的行为,如,冲入火场救出动弹不得的儿童,我们通常认为这值得高度的赞扬,但并非必要;而效益主义则认为,既然这一行动能够增加总体福祉,那么它也是我们的道德责任。换句话说,
公平性
之前提过,公平性是效益主义的优势之一,试想百万富翁和街边乞丐的福祉重要并同等重要,这一信条是多么美好!
但,代价是什么呢?
「公平性」在道德共识中似乎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我爱我的孩子甚于你的孩子,我爱我的朋友甚于陌生人,我爱我的邻人甚于大洋彼岸的人。如果我的孩子犯了牙疼,我会将钱用来送他去看医生而不是捐给遭受饥荒的儿童;这非常自然,但前者带来的总体福祉却远小于后者。
效益主义是否会判定这样的行动为不道德呢?
反驳:效益主义者认为,这一行动不是不道德的,但并非我的孩子比贫困儿童「更重要」,而是因为将钱捐给遭受饥荒的儿童从长期来看也许会比送孩子去看牙造成更多的痛苦(自己的孩子会认为父母不重视自己,从而导致长期的发展阻碍;而遭受饥荒的儿童与我素不相识,也不会因为我「不捐献」这件事造成更大的伤害)。通过这种论述,效益主义者说,更关注与自己亲近的人实际上是更能增加总体福祉的。
但公平性的问题不仅如此。由于我们必须平等计算所有人的福祉,试想在一个社会中,几乎所有人都对一个小型少数群体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并以此为奴隶制辩护。
如果遵循效益主义的原则,在作决定时,我们不仅要考虑被奴役者所受的痛苦,也要考虑奴役者的快乐。这就不可避免地导向「多数人的暴政」——
本质善恶的模糊
For utilitatians, the morality of an action always depends on its results. This feature of the theory is precisely what supports its moral flexibility: any sort of action can be morally right, so long as its outcome is optimific.
效益主义的道德灵活性同样也有其另一面,那就是行为本质善恶的界限被模糊了。我们倾向于认为,杀人,强奸,奴役这些行为,从本质上就是「恶」的;效益主义则不苟同「本质恶」的概念,因为一个行为的善或恶,与其本身无关。
想象这样一个人,他没有亲近之人,生活如同行尸走肉,未来黯淡,整日与抑郁相伴。他仍然想活下去,并偶尔能获得一点微小的快乐;但就整体而言,他是痛苦的,并且比绝大多数人都痛苦,我们知道这一情形不会改变。
这个人的生命本身降低了总体福祉,如果他死了,世界上的痛苦将会减少。因此,假若我们能在不造成更多痛苦的前提下杀死他(如,伪造死因为自然死亡并不被任何人发现),我们就完成了效益主义提出的道德要求。
这不是谋杀,而是正当杀人(justifiable homicide),正如在极端情况下食用人的尸体一样。为了「最大化福祉」,没有什么禁忌是绝对的。
如何,你能接受吗?
事实上,许多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的人都曾以类似的逻辑为自己辩护。我们深知他们的虚伪,但以效益主义的角度看,其中也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故事总是类似:没错,我们不完美;但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大多数。就算推翻我们,你确定会有更好的结果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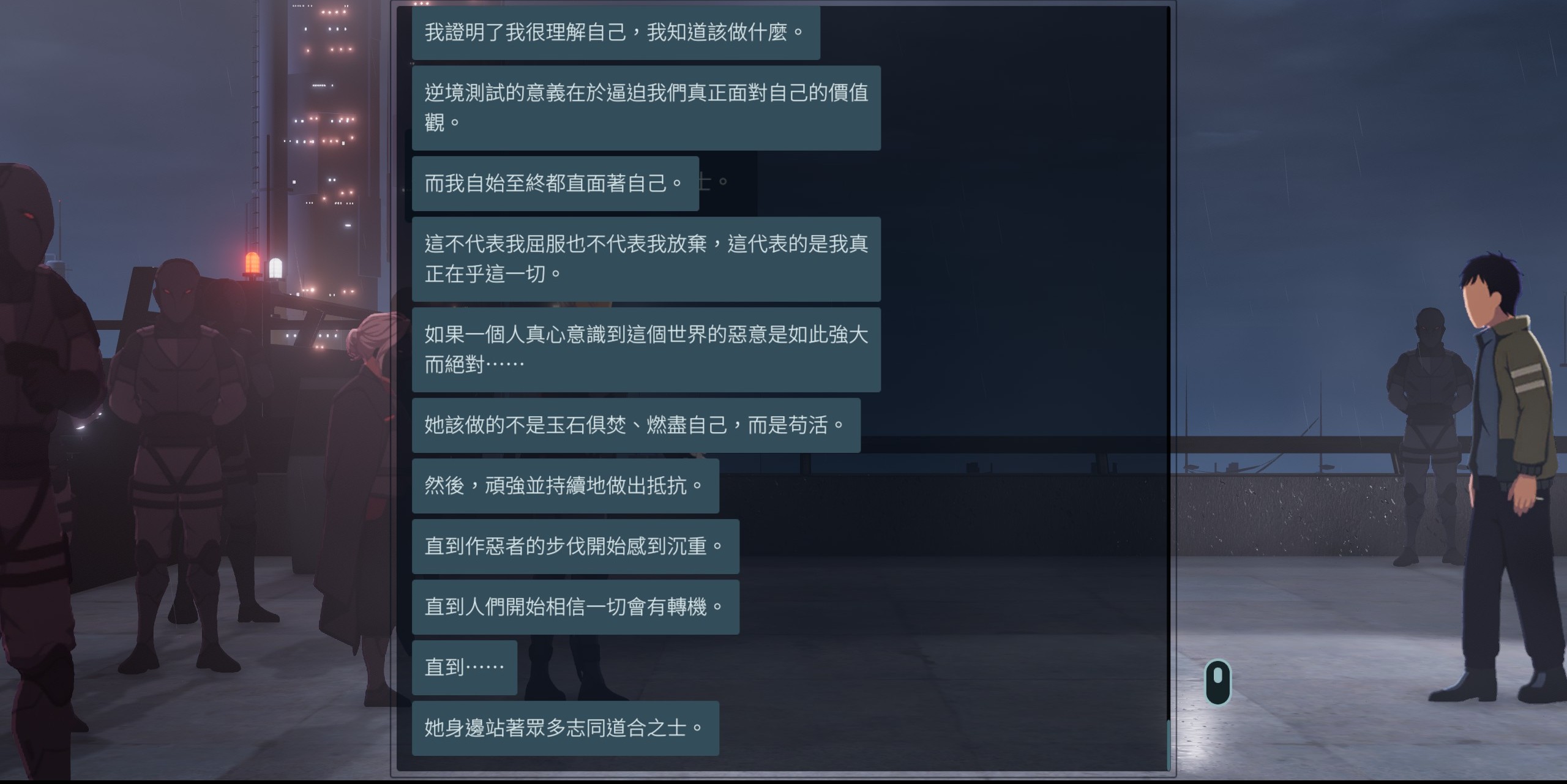
「听着,这不是童话世界,」效益主义者们说,「我们可能不得不与邪恶合作,为了最小化造成的痛苦。」在这里,也许「意图」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做出判断。这些话语所表达的,是对总体福祉的真切关注,还是逃避责任的自我安慰?
非正义
It’s true that, when rights are violated, victims are usually harmed. So utilitariansim usually condemns injustice. But not always.
在这里,我们将「正义」定义为对权利(rights)的尊重;反之非正义则是对权利的侵犯。效益主义要求我们,即使行为非正义,只要它是最优的,我们就应当采用;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
比如说,执法者通过威胁、关押甚至惩罚犯罪分子的亲人,能够有效的迫使其自投罗网。如果这样能够增进总福祉,效益主义认为可以接受。但这一行为侵犯了无辜的人的权利,是非正义的。
二战后美国遮掩了纳粹科学家的罪行,因为他们愿意分享战争科技;执法人员承诺释放罪犯,如果他们愿意透露有关头目的情报;中饱私囊的政治家能够安享晚年,仅仅因为追责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动荡 —— 我们对这些非正义的事件一点也不陌生。效益主义将受害者的痛苦与「总体福祉」放在天秤上衡量后,将它们视为道德上善的。
一个可行的道德理论,应当给予「正义」应有的重要性;但效益主义在这方面似乎并不令人满意。反对者们藉此提出另一个论述《论非正义》Argument from Injustice:
- 正确的道德理论不会要求我们采取严重非正义的行动。
- 效益主义有时要求我们采取严重非正义的行动。
- 效益主义并非正确的道德理论。
反驳 2 => 前提 2:「非正义」的行为一定不是「最优」的。这本质上又是一种采取「道德无知」回应的策略。找到反例并不难:我们不得不承认,有时非正义之举能够达成最好的结果。
反驳 3 => 前提 1:「正义」的牺牲有时是必要的。这也许是最适合效益主义者的宣言了。毕竟,从效益主义诞生之初,它就做好了与主流意见背离的准备。